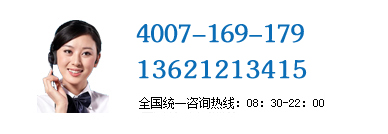孙庆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在这场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徙中,乡村的社会生态日趋瓦解,乡村教育因远离乡土而陷入失忆的窘境。因此,重申农村教育的使命,拯救行将消逝的记忆,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关乎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发展战略。
农村教育的处境
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几乎与乡村生活无关,那些曾给乡村人带来灵感、幸福与希望的教育已更换了门楣。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这些数字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写照。在这种背景下,农村教育更因落入“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而面临深度危机。由于缺乏反哺乡村的机制,农村教育在乡村曾经发挥过的功能几乎消失殆尽。其突出表现:一是以为城市培养人才的目标背离了乡村发展的本位,农村教育难以惠及乡土,反倒培养了在心理上与乡村生活游离的一代。二是在城市导向的课程体系中,延续千年的乡土知识备受冷落甚至贬抑。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依旧支撑着农业系统的生产和生活知识,被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落后的废弃之物。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几乎与乡村生活无关,那些曾给乡村人带来灵感、幸福与希望的教育已更换了门楣。与此相应的是,城市化的优质教育深入人心,业已成为乡村父母改变其儿女命运的心理动力和行动上的必然选择。
农村教育的问题早已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并在制度设计层面寻求出路。农业部从1990年开始在全国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并于1994年在全国全面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2001年,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农村普通初中试行“绿色证书”教育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意在对农村初中学生进行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教育,既为学生升学奠定基础,又为他们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创造必要的条件。遗憾的是,单一化的应试教育和单向度的城市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致使《指导意见》在操作上难以持续。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政策隆重出台却又不得不悄然落幕。
乡土失忆的现实
孩子们可能还生活在乡间,但山上的动植物与他们无缘,触目可及的河水因封闭的校园而无法亲近。更有甚者,对自家屋舍前后种植的蔬菜也全然无知。
从乡土知识的传承来看,乡村文化处于断根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为了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陪孩子进城读书已成为乡村普遍的事实。这种教育改革政策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割断了孩子与乡土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寄宿制使孩子与家庭生活游离,父母带给他们的呵护与日常生活的影响甚为缺失。我们在河北、河南和陕西的调研发现,寄宿制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他们可能享受了那些懵懂的教育资源,却失去了儿童成长中家庭教育的健康底色。那些基于家庭生活的民俗养成,那些在润物无声中习得的生活常识,对于寄宿的孩子来说,将是终身难以弥补的缺憾。
第二,与自然环境相对疏远,言其相对,是因为他们可能还生活在乡间,但山上的动植物与他们无缘,触目可及的河水因封闭的校园而无法亲近。更有甚者,对自家屋舍前后种植的蔬菜也全然无知。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于农业的认知、对乡村的记忆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出人头地,告别乡土。
第三,对于家乡的历史处于无知的状态。了解家乡的历史是爱家乡的重要前提,是生成情感认同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无论是家乡的历史人物还是重大事件,对于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而言都是陌生的。他们不了解家乡的历史,更不以此为荣,心念所至就是要逃离乡村。
第四,对村落礼俗漠然无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与农民的时间经验一体,记录着乡村的时序刻度,承载着小农以礼俗活动为核心的生活内容。然而,这些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礼俗传统,这些被视为乡村生活灵魂的仪式活动,渐已远离了孩子们的生活。
严峻的状况不止如此,我国目前除了6973万的留守儿童之外,还有3581万的流动儿童。调查数字显示,流动儿童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平均时间长达3.7年,其中7-14岁流动儿童中约三分之一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在6年以上。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有半数以上流动儿童与户口登记地在日常生活上基本没有联系,超过半数的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称。面对如是这般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辈辈相承的生活记忆是否还能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当作为实体村落的故乡渐行渐远,作为精神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是否还能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否还能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因此,集体记忆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媒介。相形之下,我们已经面临集体失忆的时代,这种失忆会使乡村青年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使乡村少年失去了家乡情感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期待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注重开掘乡土社会的本土资源,把地方特色文化转化成了内发性的教育资源。
当没有了学校的乡村和没有了乡村的学校已变成了普遍存在的现实,当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童遭遇“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的窘境,文化记忆能否成为链接过往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的精神纽带?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MarieRoue)通过对加拿大詹姆斯湾世代聚居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二战以后,加拿大政府把印第安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目的是让年轻的印第安人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变成普通的加拿大公民。然而,结果并未如愿,学校教育使年轻人远离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却没有使他们获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也失去了祖辈在山林中生存的本领,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克里人将歧途中的年轻人送到克里人祖辈的狩猎营地,使它们学会克里语言,重新获得捕鱼、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呈现了自然与文化环境特定的力量。这些重归土地之后的年轻人,重建了他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活出了自己的自信,建立了自身与祖居地之间的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老一辈克里人依靠回归土地的方法,医治了教育的创伤,拯救了迷失的一代。这个故事说明了乡土的特殊意义,也为人们在现代魔性造就的不安中寻求生活的本质,开启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
无论我们对“回归土地”和“留住记忆”报以怎样复杂的情感,无论是将其视为无力与主流抗击的逆流,还是将其定位成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畅想,我们都必须思考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村落彻底消失,农民彻底终结,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人口学家的预测已经对此做出了否定性的答案―――再过40年,中国还将有五亿人生活在乡村。基于这样的国情,我们接下来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如何让乡村教育回归乡土以传续记忆的根脉?
教育存留乡土与抗拒失忆的使命如此紧迫急切,那么,扎根乡土的教育又该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呢?实际上,我们调查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注重开掘乡土社会的本土资源,把地方特色文化转化成了内发性的教育资源,例如河南辉县川中幼儿园形成了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生存与发展之道。60亩的生态种植园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强化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听闻自然界的声响,让他们在播种、观察秧苗生长和收获果实的过程中,尽享植物成长与自我成长的快乐,让他们种下爱心,拥有责任心。幼儿园从课程设计入手,将乡村的自然资源转变成为课程资源:河滩里的卵石成为孩子们作画描摹的艺术品;玉米皮在手工制作中华丽转身为小拖鞋、小靠垫和不忍再触摸的盛开的花朵;废弃的竹帘变成了风筝的龙骨;丢落的纸箱竟然幻化为墙壁上悠然的舞者。尤为可贵的是,“妈妈创业队”向新一代已不熟悉农业的农民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不仅使孩子不再成为留守儿童,也让麻将桌前的妇女拥有了服务家庭、服务社会的尽职生活。在让孩子们享受优质的乡村教育的同时,也让学校因凝聚周边村落而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案例,总会点燃我们在“土地的黄昏”中通过教育重建乡土的希望。
在城镇化日益成为乡村发展的主流话语之时,我们却强调“回归土地”,也许这是与凯歌高奏的城镇化并不协调的另类音符,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乡土性”却是对文化记忆最深层的唤醒,因为,一个有深度的社会,必须拥有自己的社会记忆,这是世代之间维系共同情感和深厚凝聚力的心理基础。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