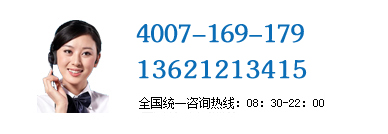幸福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偏差机制
[摘 要]: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 这三者有极其重要的本质差异, 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次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 立体地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 (2)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 (3)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 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 预期、即时和回忆三种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 对政府管理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 避免"牺牲体验追求指标", 解决"幸福悖论", 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问题提出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话题和终极目标, 很多人都预期财富增加幸福感会随之增加。但是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在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指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 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 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 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这一现象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一提出, 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与幸福"的研究热潮。为什么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感的同步增长?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等学者在《科学》杂志发表"假如更富有了你就更幸福吗――焦点错觉" 一文。他们指出:高收入与好情绪相关的观念很普遍, 但通常这是个错觉。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拥有相对高的生活满意度, 但是在即时情绪体验方面却几乎不比他人更快乐, 而倾向于更紧张, 更没有时间花在特别享乐的活动上。而且, 收入对于生活满意的效应是非常短暂的。人们往往夸大了收入对于快乐的贡献, 其原因是他们在评价自己或他人的生活时, 往往聚焦于某一方面的成就, 出现了焦点错觉(Kahneman & Thaler, 2006)。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幸福研究中, 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收入或其他物质因素将产生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可能导致重大决策错误。同样, 对于其他影响因素的聚焦, 也会导致聚焦错觉和决策失误。因此,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和Stone (2004)提出, 幸福感的实质是在行动过程中产生的快乐等积极情绪体验, 不能简单地用满意度调查进行衡量, 用体验效用来度量幸福能够更加反映幸福的本质。他将体验效用进一步区分为预测效用, 即时效用和回顾效用(刘腾飞, 徐富明等,2010)。预测效用(predicted utility)是指个体关于将来某个时刻的体验效用的预期和信念; 回顾效用 (retrospective utility) 是基于对事件或者一段生活的回顾性评价, 是在记忆基础上对体验效用的测量; 即刻效用 (real time utility)是对个体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体验到的快乐或者痛苦的即时测量, 是在体验过程中对体验效用的测量(Kahneman, 2000)。这几种不同形式的体验效用之间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 可以引发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例如, 为什么决策结果的决策效用不同于体验效用?为什么回顾效用、即刻效用、预测效用三种不同形式的体验效用之间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哪些决策偏差和非理性?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 学术界对幸福感的调查测量, 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分开进行的。大多数涉及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考察的是单层面的幸福感调查, 而对于幸福体验的心理机制与生理机制探讨较少。
基于此, 要真正实现对人们幸福体验的全面认识, 需要一个全新的整合的研究思路。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预期幸福、即刻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 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和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 拟解决以下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 预期、即刻和回忆三种体验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 对于指导人们正确的生活观念, 防止人们"牺牲体验追求指标", 解决"幸福悖论", 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同时也能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信息。
以往研究回顾与评价
回忆效用的偏差及其心理机制的文献回顾
Kahneman等 (2004)提出, 对体验的回忆性报告是不可靠的, 真实的体验只能通过基于时刻的、当下的以及整个持续过程才能更可靠地被测量。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 依然有很重要的理由关注回忆体验。不像当前体验是"客观"体验的有效测量, 回忆测量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行为, 人们主要根据回忆体验来决定未来的行为选择(Wirtz, Kruger, Scollon, & Diener, 2003)。Wirtz等人(2003)分别测量了被试在假期开始前、假期中以及假期结束后的正负性情绪体验, 并询问被试是否愿意再过一次这种假期。结果表明, 回忆和预期的情绪体验比即时的情绪体验更强烈, 回忆的正性情绪越高, 则被试越愿意重复这个假期体验, 当即时与回忆体验不同时, 回忆体验指导人们未来的决策。总之, 回忆测量比即时评估能更好的预测未来的决策。
回忆效用偏差
研究表明, 人们对事件的记忆常常与他们在事件中报告的基于时刻的体验不一致, 即回忆效用会出现偏差。一项研究中, 对骑自行车去加利福尼亚旅行的人进行调查发现, 即便旅行中连续不断地下雨、有让人不快的同伴和身体的疲惫, 人们的回忆体验还是很美好(Metchell, Thompson, Peterson, & Cronk,1997)。Kyung, Menon和Trope (2010)发现, 思维模式的不同会影响在记忆中对过去事件的重构, 导致回忆效用偏差。Levine和Safer (2002)在文章中提出, 当前情绪、认知评估、应对经历和个性特点都与过去情绪的记忆相关, 某些因素的变化也会导致对情绪的记忆出现偏差, 这一偏差反过来又影响未来的计划和情绪(Levine & Safer, 2002;Morewedge,Gilbert, & Wilson, 2005)。
由于体验效用是正负性情绪的总和, 因此许多研究者通过研究对情绪的记忆探索回忆效用偏差机制, 如果对情绪的记忆不准确, 那么回忆效用也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偏差。有些研究者认为, 对情绪的记忆是可靠的, 情绪记忆不会出现偏差。例如, Brown和Kulik (1977)认为, 情绪作为意外和重大事件的特征, 尽管时间流逝, 却仍旧会保持逼真的记忆。根据LeDoux的观点, 对情绪体验的记忆是永久存储的, 并且相对于对这些事件本身的记忆, 是由不同的脑区调节的。类似的, 还有学者提出,由于情绪是与皮下动机系统紧密相连的, 因此它们很容易被记起, 并能抵制消逝。这些观点都是部分基于以下的发现提出的:经典条件回避反应尽管消逝, 一旦再次暴露于压力刺激之下, 便能得到迅速恢复,这一点类似于情绪的再现。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情绪并非直接存储在记忆中的, 而是基于对情绪诱发环境的记忆而重构的(Levine, 1997), William James认为, 情绪是重构而非回忆的, 回忆过去诱发情绪体验的环境能够使人们在当下体验到一种类似却全新的情绪体验。不少测量情绪记忆准确性的研究也发现, 相对于直接提取, 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至少是部分重构的。学生在回忆考前焦虑情绪的强度时(Devito & Kubis, 1983; Keuler & Safer, 1998), 人们在回忆他们献血前的焦虑程度时(Breckler, 1994), 以及精神病人在回忆过去的抑郁症状时, 都倾向于高估过去的负性情绪。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要求人们估计先前日记中记录的情绪体验的平均强度时, 个体会同时夸大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的强度。这些研究都表明, 人们对过去情绪体验强度的记忆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钱国英,2008)。
回忆效用偏差的内部心理机制
(1)情绪记忆的重构
对情绪记忆偏差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便是基于阿诺德的情绪理论――认知评价理论对回忆效用偏差机制进行的探索(乔建中,2008)。根据阿诺德的情绪理论, 情绪体验是通过对刺激事件的评价诱发的。评价是指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刺激与其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评价(Lazarus, 1991)。当人们评估环境与自身目标、愿望或价值相关时, 就会体验到情绪。特定类型的评价又会诱发特定的情绪反应。基于这一理论, Levine (1997)提出了情绪记忆的重构模型(general model of reconstruction of memory for emotions)。Levine提出, 当个体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存在空缺时, 人们就会根据对刺激事件及其评价的记忆重新构建情绪记忆。从刺激事件发生至今, 如果他们对事件的评价发生了变化, 那么对情绪体验的记忆就会出现偏差, 且这一偏差方向与评价改变的方向一致。这一模型总结并拓展了之前的研究, 表明当前的态度和动机导致对过去态度和事件的回忆出现偏差。
情绪记忆重构模型主要探讨了当前评价在情绪记忆中的作用。也就是说, 当个体对刺激事件的当前评价(current appraisals)与原始评价(initial appraisals)不一致时, 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就会出现偏差, 且偏差的方向取决于评价的改变。Levine利用1992年Perot7月份宣布退出美国总统竞选这一事件, 以Perot的支持者为被试, 通过问卷和电话访谈, 收集了被试在7月份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情绪体验(悲伤、愤怒和希望)以及评价和10月份总统竞选结束后对最初情绪体验(悲伤、愤怒和希望)的回忆以及当前的评价。根据被试前后评价的变化情况, 将被试分为三种, 忠诚组(一直支持Perot), 回归组(听到消息后支持别的候选人, 但在竞选时再次支持Perot)和背弃组(听到消息后以及竞选时都支持别的候选人),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三种不同的情绪体验, 回忆的强度和最初报告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并且情绪和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也就是说, 认知评价的改变, 导致对情绪强度的回忆也会有所改变。例如, 对于忠诚组而言, 被试显著低估了悲伤和愤怒情绪的强度, 高估了希望情绪的强度; 对希望情绪而言, 组别的主效应显著, 忠诚组显著高估了希望情绪的强度, 回归组准确报告了希望情绪的强度, 而背弃组则显著低估了希望情绪的强度。
由此可见, 对刺激事件的当前评价确实会影响个体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但是关于情绪记忆的重构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回忆过去的情绪体验, 这一准确度可能揭示的是正确的重构, 也就是说个体正确的回忆了刺激事件以及对刺激事件的相关评价。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情绪也有可能是之前存储在记忆中, 但是又不可避免的在提取过程中受到扭曲, 因为最初的记忆痕迹受到当前评价的调节。
因此, 我们认为, 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 受到当前对刺激事件评价的影响。个体在回忆过程中, 除了直接从记忆中提取支持当前评价的情绪信息, 还会根据当前的评价去重构当时的情绪体验, 这两者共同构成对过去情绪体验的记忆。
(2)峰终效应和持续时间忽略:
另一个导致回忆效用出现偏差的因素便是"峰终效应和持续时间忽略", 即人们在回忆体验时, 主要依赖于最高点和终点时刻的体验, 而忽略持续时间、平均值或者体验总量。例如, 让地铁乘客回忆一次或者多次他们错过地铁的经历, 再预期未来错过地铁的感受。回忆一次经历的被试会选择一次最糟糕的经历, 他们预期未来错过地铁比回忆多次经历的被试有更负面的体验。
Kahneman等人(1993)用3个冷压力实验证明了人们在回忆过去体验时出现的持续时间忽略和峰终效应。实验要求被试把手放在冷到能够感到疼的冷水里, 直到实验者允许把手拿出来。第一个短时间实验中, 被试把手放在华氏14度的水中60秒, 第二个为长时间实验, 也是要求被试把手放在14度的冷水中60秒, 然后手继续放在水中30秒, 并将水温逐渐升高到15度。两个实验间隔7分钟。被试逐一报告他们体验到的疼痛强度。短时间实验中, 被试报告的疼痛强度为8.4 (0~14), 长时间实验中, 被试报告的疼痛强度为6.5。第二个实验结束7分钟后, 询问被试愿意重复哪个实验作为第三次实验, 32个被试中22个选择重复长时间的实验, 也就是他们选择多承受他们完全可以避免的30秒中的疼痛感。80%的被试说最后的30秒可以减轻疼痛感。
在结肠镜检查实验中, 出现相同的结果(Redelmeier, Katz, & Kahneman, 2003):让正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病人每60秒在0~10分量表上报告一次痛苦程度, 然后报告对整个过程的总体评价。结果发现顶点和终点的测量与病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关是0.67, 而检查的持续时间与病人后来的总体评价只有0.03, 出现了持续时间忽略。这项研究之后, 研究者进一步进行了临床实验(Redelmeier, Katz, & Kahneman, 1997)。把正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病人随机分配到一种实验条件下, 即检查结束后延长了一分钟的检查时间。在这一分钟里, 结肠镜保持静止不动, 引起了中等程度的不适感, 但比之前检查时的痛苦程度要轻得多。被试在回忆检查的疼痛感时, 有一分钟停留的检查疼痛感更小, 被试更愿意接受第二种检查方式。
噪音实验中同样发现(Schreiber & Kahneman, 2000), 在一段令人不悦的噪音后面加入一段分贝降低的噪音, 使得这一段噪音变得不那么让人回避而更可能被选为重复的实验。Schreiber和Kahneman (2000)的研究中, 实验者向被试呈现一系列的噪音刺激, 要求被试在刺激呈现过程中进行即时评价, 在刺激呈现后对该组刺激做出总结性评估。结果发现, 利用即时评价的顶点和终点可以预测和解释98%的系统变异; 而且更有趣的是, 要求一组被试对连续16秒的78分贝噪音刺激的不舒适度进行评价, 另一组被试对在第一组刺激基础上再加上连续8秒的66分贝的噪音刺激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被试对第二组刺激的不舒适度的评价显著低于第一组, 出现了持续时间忽略效应,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说明人们在回顾效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Diener (1999)等通过对生活的评价研究同样验证了回顾效用偏差的存在。
所有这些实验中, 如果用语言描述实验程序, 被试都会选择持续时间短的实验操作, 但是如果让他们回忆自己的体验, 大部分被试都倾向于选择持续时间长的实验, 因为回忆体验时, 被试只回忆体验中离现在最近时刻的感受, 或者感受最强烈的时刻体验(峰终时刻), 而忽略了持续时间这一影响总体体验效用的因素, 导致回忆效用出现偏差。
综观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发现, 回忆效用出现几个普遍的判断偏差:(1)顶点-终点效应; (2)持续时间忽略((duration neglect); (3)更好的终点影响回忆效用评价; (4)更好的始点影响回忆效用评价; (5)对过去事件的当前评价影响回忆效用。我们认为, 回忆效用是基于回忆的基础上对事件或一段时光的回顾性评价, 人们在回顾评价的时候, 记忆以及记忆信息的提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回顾评价时, 人们究竟在大脑中提取哪些信息(如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及信息的提取先后次序是决定回顾效用的一个重要因素。